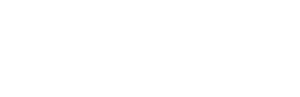一般认为,8000年前的人类还处在一个没有任何金属工具的年代,中国的学者们将这时归纳为新石器时代。古代先人以磨制石器的方式制作生产工具,但就在这样一个原始石器时期的年代里,复杂而精美的玉器却不可思议地出现了,在现在的专家们看来,即使用现代工艺来制作这样的玉器,也是相当困难的。
那些近乎鬼斧神工般的古代玉器,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?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今天,这样的问题,我们只能通过古代器物本身的研究来回答了。
玉石是一种硬度极高的天然矿物,用今天的铁质刀具也很难在上面留下划痕,而现在发现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古玉器外壁,却刻满了神秘的纹饰……
玉琮是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,距今是五至八千年的历史。古人的玉琮造型复杂,上面的纹路细如发丝,不仅如此,玉琮的中心还被掏出了一个圆润而匀称的圆孔,外面则是对称的方形结构。这种被认定为祭祀器的玉器,最早形象地记载了中华民族“天圆地方”的地理概念。而除去祭祀再无合理解释用途的红山文化的玉龙,则可物证中华民族最早的图腾崇拜。
在今天的制玉工艺上,已经很难看到传统工艺的影子了。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,古代制玉工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,传统的手工工艺完全被一种全新的现代工艺所取代,今天的制玉工具用电能作动力,磨制的钻头采用特别定制的金刚钻。金刚钻的硬度远远超过了天然玉石,在电动工具的带动下,可以轻易的把玉石切割出各种形状。
一块已经基本琢制完成的古代玉璧,出土时上面残留了大量的沙石,这些看似普通的砂石的出现,揭示了古代制玉工艺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,当年,考古人员细心的把这些砂石保留在了玉璧的表面,拍摄了珍贵的出土照片,也成为今天解开古玉琢玉之谜的大门。
从最直接的方式去理解古代的制玉工艺,有一个环节至关重要,那就是找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物质,只有这样,玉器的制作才有可能完成。
经过检测,这些残留的砂石矿物学成分是花岗岩,而其中石英石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。石英石是一种高硬度的矿物,它的硬度可以达到7度,而通常,玉石的硬度不会超过6.5度,它使玉器的磨制有了可能。
那么,这种高硬度的砂粒,古人是如何找到的呢?
一种观点认为,砂子都是玛瑙、石英或者是燧石粉碎了,质地软一些的材质,化成了粉、泥土,而那些坚硬的颗粒却保留了下来,那就是俗称的“砂子”。所以中国任何地方的砂子,硬度基本都在7度左右,砂子永远是砂子,不论经过几千万年也是砂子,这种砂子由于硬度都比较高,所以人只要到河边把砂子运过来,再把比较轻的淘掉,简单地选择纯度、硬度、颗粒大小一样的石英砂,就可以做解玉砂了。
原来,这些看似普通的砂粒,竟然是大自然的杰作,在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风化淘洗作用下,最坚硬的砂粒被保留了下来,它们是天然岩石中最坚硬的部分,而古人则凭借他们的智慧,找到了解玉时最有效的一种天然工具。
毫无疑问,用这些高硬度的砂石可以轻易的在玉器表面留下划痕。但令人费解的是,像玉琮这样工艺高度复杂的器物,仅仅依靠简单的手工刻划,无论如何是难以完成的。
与“良渚文化”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,出土了大量的玉器,这些玉器有着各种各样的造型,有的采用立体的圆雕手法,有的是镂空的透雕。可以想见,这些玉器的制作需要历经不同的加工工序,从最初的玉料切割,到器型的简单加工,直至刻划纹饰,钻孔打磨,工艺严格而复杂,可是,这些融合了各种高难度工艺的玉器,又是在什么工具的配合下才能完成的呢?
这些玉器的年代同样横跨了5000多年的历史,它们就出土在和玉琮相同文化区域的墓葬群中,看上去这些玉器造型奇特,似乎并不是古代玉器中常见的器型,有的被切出两道深深的沟槽,有的只是一个光滑的圆柱体。
考古学家经过仔细鉴定,发现这些玉器其实是古人琢制玉料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半成品,而有的则是废弃的边角料。正是在这些造型不太规则的玉料上,令人惊喜地保留下了当年制玉工艺的不同环节。
古代玉器的研究人员根据这些带有制作痕迹的古代玉料,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古代制玉工艺的大致面貌。
距今7000至5000年,是中国的新石器从中至晚期。这时,古代玉器制作达到辉煌的一个巅峰时期,这一时期的古代玉器,从北方的“红山文化”到南方的“良渚文化”,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珍品。
古玉器的表面,常常残留着一些奇特的弧形切痕,专家推测,这些弧形切痕保留了当年一种线切割工艺的痕迹,线切割是制玉工艺的第一道工序,专家称之为“解玉”,所谓解玉就是把玉料按照玉器成品的需要,切割成不同的形状。
专家们认为,这种切割是线切割,而线切割的线就是兽皮。因为猎得兽以后,兽皮被剥下来,可以割成小细条,然后卷成绳子状,因为它本身有坚硬程度,然后加上解玉砂,在一块石头上反复这么拉,解玉的方法就形成了。经过有的考古学家实验,一块10公分左右的玉料经过兽皮加解玉砂反复拉磨,在几十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割断玉料。
当然这种皮条解玉也只是推测,新石器时期,古人也有可能用木片、竹片等片状物代替皮条来解玉。也有人认为只是用木片、石片或者是竹片,而没有其它的工具。而无论怎样,古人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,创造性地做出一种比玉石更硬的材质,用来大规模地制作玉器,因为自然界即使有当时也无人能运用那些材质。
在当年出土的玉器上,大多有一个圆孔。这些圆孔有的是出于器物造型的需要,有的则是为了系挂佩戴。这些穿孔有的细如针眼,有的直径达四五厘米,这些圆润的孔洞,古人又是如何穿凿的呢?
一些用黑石英制成的钻头出土在江苏省的丹徒县,黑石英的硬度是7度,专家经过实验,将钻头装在木柄上,通过人力便可以在玉料上打钻出孔洞。
像新石器时期玉器上的穿孔,或许就是用这种工艺制作而成的。现在的研究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的:一个桯子,一个杆,然后头上有解玉沙,通过某种转动,有可能是拉杆的这种转动,也有可能手搓着转动,可能还有其他的转动方式,然后把桯子转动先把孔打出来。
但是,在同一时期出土的玉器中,有些钻孔的直径宽达5厘米,这么大的钻孔显然不可能用同样的钻头钻制,古人会有什么独特的工艺呢?
一块出土于山东的玉料解答了后人的困惑。这是一件古人经过打钻的玉料半成品,中间是孔芯,边上有着明显的钻痕。可以肯定的说,大部分玉器都是通过空心钻打出来的,因为它打的非常规范。
据推测,当年的管钻或许就是用天然的竹子做成的,考古发现中还出土了当年用管钻钻孔留下的孔芯,古人用管钻钻孔时,由于当年的工具简陋而难以准确定位,在不少的玉器上还留下了错位的痕迹。
钻孔技术和线切割工艺的综合运用,使古代玉器的透雕工艺有了可能。
在新时期时期的玉器上,最让后人不解的是那些工艺极为繁复的神秘纹饰,在坚硬的玉石上雕刻这些精美而细密的线条,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艺。
有的考古学家认为,这些纹饰虽然精美而且复杂,但是除了手工制作之外,似乎也找不到更合理的猜想。
在江苏的一个古遗址上,出土了200多件尖状石器,这些石器的硬度大多超过玉石,而且有着锋利的尖头和弧形的薄刃,专家认为,这些石器可能就是用来雕刻玉器纹饰的工具。
还有的专家有着更大胆的猜想,他们认为是用鲨鱼的牙齿雕刻的。在良渚的一些墓葬里,发现了古代的一些鲨鱼的牙齿,由于鲨鱼牙齿非常坚硬,有些人就认为说,可能一些微雕的图案是用鲨鱼牙齿来刻划的。
持这些观点的专家们认为,不论是用尖状石器还是鲨鱼牙齿,它们虽然简陋,但在有着丰富经验的玉工手中,雕刻那些复杂的纹饰似乎也是可能的。
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却有着不同的看法,他们认为,这些神秘的纹饰用纯手工方法雕刻是不可能完成的,在当时,应该已经出现了制作玉器最关键的工具——原始的砣机。
砣机是中国古代制玉工艺中最重要的一种工具,它的出现,带来了古代制玉工艺最具革命性的变革,一直到解放初期,古老的砣机仍在使用。
砣实际上就是各种圆形的工具,砣有金属的,有不是金属的,石头也可以做砣,木头也可以做砣,皮子当然也可以做砣。在传统制玉工艺中,砣机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。
由于砣具是圆形的片状物,旋转起来之后,可以提供均匀而有规则的摩擦力,通过砣机的连续转动,熟练的玉工再调整玉料的不同位置,便可以随心所欲的雕刻出各种形制的玉器,如果没有砣机的出现,仅仅凭借手工的雕刻,制作那些鬼斧神工的珍品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们看到有一些古代的纹饰,有的曲线非常漂亮,非常规矩,那只有拿砣这个工具做得出来。
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还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:1987年,在浙江“良渚文化”的遗址中,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玉杆纺轮。
这件原始纺轮的玉器模型记录了当年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,但是,玉器专家却从中看到了另一种含义——这件玉纺轮造型酷似后世的砣机,专家认为,如果让这样的玉纺轮转动起来,用它磨制玉器是完全可能的,而另一方面,它还证明了既然在当年有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,说明制作转动的工具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
专家们对史前玉器是否应用了原始砣机还存在分歧,但当他们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商代玉器上时,他们的结论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。
专家们相信,制作如此众多的精美玉器,没有砣机的参与,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专家们断定,这些玉器已经远远超过了纯手工雕刻的极限。这一时期,一定出现了工艺上非常完备的砣机,而商代发达的青铜工艺无疑给砣机等相关工具的制作提供了可能。
也有人认为,像商代的一个玉簋,只有10公分大小,但制做起来很难,要把它做规矩了、做圆了,要复杂的多,所以有人说,在商代的玉簋是玉器制作的一个分水岭。
专家推测,像殷墟出土的小玉人和动物形玉器,应该都是用砣机制作完成的。从这一时期开始,砣机显示了它作为工具的巨大能量,除了大型玉料的切割和钻孔之外,几乎所有的琢制工艺都可以用砣机来完成。但遗憾的是,在所有商代的考古发掘中,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件制作玉器的砣具,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?
有人认为,当时青铜是比较贵重的金属,它坏了以后就被熔化,熔化又去做新的,所以我们在发掘的时候,很少发现破的青铜器,很少发现青铜工具,因为它又重新回炉了。
虽然后世的研究人员没有找到商代制玉工艺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,但是到周代,一本名为《考工记》的古文献记录了周王室的制玉工艺。
《考工记》的记载中说,周代王室里分成了6种不同的手工艺,而其中的玉工则是周王室最重要的一种手工艺人。
在当时的周王室和诸侯封地里,都有专门的玉工负责玉器的制作,而后世的考古发现也证实,在周代的时候,玉器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。
当历史走到东周晚期和汉代,一种全新材料的大量使用给玉器工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,那就是铁器的出现。西汉初,铁制品的工艺已经发展成熟,铁质的琢玉工具逐渐替代了青铜工具。
青铜工具硬度低,不耐磨,当铁质工具普遍使用之后,制玉工艺无疑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专家们普遍认为,到战国、汉代,那些玉器都是新疆玉,硬度很高,没有这些铁工具的制作,是出不来那种效果的。
由于铁制砣具硬度更高,耐磨性更好,这一时期琢磨的玉器不仅造型异常复杂,而且纹饰也更加圆润流畅。
还有更多的玉错金、错银、嵌绿松石、嵌宝石器物,它们的精美绝伦,巧夺天工,令人瞠目结舌。
有人说,人们之所以崇拜战国玉器和汉代玉器,是因为我们现在拿这些东西来仿都是很难的,非常之难,达不到那种效果。可以说,由于铁工具的出现,战国到汉代的玉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此后,铁制砣具成为最重要的制玉工具,它的使用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。
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期间的铁制砣机还出现了一次不小的变革,它的时间就发生在距离汉代不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。
北齐《校书图》,是一幅反映古代文人生活的绘画,年代大约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。画中的文人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校对书稿,文人的这种坐姿后人习以为常,但是,在魏晋南北朝之前,古人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坐姿。
有趣的是,古人这种生活习俗的演变却间接带来了制玉工具的改变,当高型家具出现后,古代砣机的高度也随之改变了,席地跪坐式的砣机发展成了高型的坐凳式砣机,这种高型砣机古人称之为水凳,这也就是一直到解放初期仍在使用的砣机。
有专家介绍说:一个坐凳,坐凳的高低自己可以改变,一般选择跟自己髋关节一般高的,他用两个蹬踹起来,他有那个空间就甩起来了,有时候踹的速度相当快,据说一个磨玉工一天的工作量几乎可以相当于从北京走到沈阳了。
水凳的出现解放了玉工的双脚。在席地跪坐的时候,需要两到三名玉工的配合,才可以在一台砣机上工作,有人负责砣机的转动,有人负责琢磨玉器,有人负责添加解玉沙,而水凳出现以后,古代玉工可以通过双脚的踩踏,带动砣机旋转,独自一人便可以完成玉器的制作过程。
当一名熟练的玉工可以独自操作一台砣机的时候,他完全变成了个人的创作。他可以随意调节旋转的速度和力度,不断更换大小不同的工具,它甚至还可以用锉刀更改工具的形状。
古代玉器不仅保留了年代的痕迹,还记录下了个人的风貌。
可以说,当砣机工艺融入了一名玉工的艺术追求,玉器的制作便不再仅仅是一门古老的手工工艺,人们赋予其中的是那穿越历史的艺术内涵和人文主义的精神。
到清代的时候,砣机工艺已经走向了高度成熟,这一时期,酷爱玉器的乾隆皇帝别出心裁,希望以砣机之外的工艺制作一件玉器。
玉雕高达130厘米,描绘的是秋天山林的景象,乾隆皇帝生平非常喜爱这件玉山,曾两次写诗赞叹玉工的技艺,但有趣的是,这件玉雕作品的制作却经历了一次波折,当年,用砣机制作这种玉器的工艺已经高度成熟,但乾隆皇帝却希望用一种纯手工的方法打凿出一件假山玉雕,这是对几千年来砣机工艺的大胆挑战,当年清代宫廷造办处让工匠多方尝试,最后却不得不以失败告终。玉料只好重新运送回扬州,用传统的砣机工艺,历时4年才琢制完成。
现在,这件《秋山行旅》玉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,玉雕的经历似乎正像是为了告诉后人,即使到手工艺高度发达的清代,砣机工艺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《秋山行旅》玉山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,而更像是关于一门古代工艺的历史见证。
在电动工具普遍运用的时代,制作玉器的原理与古代砣机仍是一脉相承的,不同之处是电能代替了人力、快速取代了琢磨,而解玉沙则被用电镀的方式附着到了砣具上,今天的玉工艺人手中的工具所传承的,依然是数千年前那古老而神奇的技艺。
微信号ID:shjrsc←长按可复制(每天推送最新古玩咨询免费鉴定评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