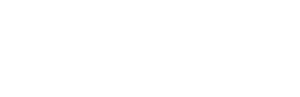诗意,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外延却又异常模糊的概念。对于诗意的表现,很难作出明确的归纳,即使是像司徒空或黄铺那样将诗和画分别列为“二十四品”,也仍然无法穷其丰富和微妙。不过,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,这两点是第一、诗意是美的,这种美既包括了优美,也包括了壮美,或者说既包括了阳刚之美,也包括了阴柔之美;第二、诗意是含蓄的,这种含蓄,意味着其美学取向是淡,是清,是静,是远,是“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”,是“当使人疑,又当使人疑而得之”。
关于第一点,其意不言自明。美,是艺术的本质属性,不美的东西是很难称之为艺术的(西方现代艺术中的“审丑”现象,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,它与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和人对这种异化的反抗有关,此处不作展开)。现实生活中不美的东西,有时甚至是丑陋的东西,一旦进入艺术的领域,也应该具有相应的美感,否则,便只能是低层次的自然主义。因此,在齐白石的笔下,不但锄头、扫帝这些寻常的田用之物是美的,而且即使是老鼠、小猪这样的较为“丑陋”之物也是美的,也显得那么楚楚动人,活泼可爱,其理由即在于此。而诗意则是美的浓缩,美的极致。在中国画的创作中,但凡是优秀的作品无不是充满诗意的,不论是山水画的气象之美,人物画的情态之美,还是花鸟画的格调之美,实际上都是一种诗意之美,或者说是一种诗意的外化,很难设想一个缺乏诗意的作者,是能够表现出山水、人物和花鸟的美感来的。而关于第二点含蓄则更重要。含蓄,是诗的特点。所谓“诗无达话”,除了诗的含意具有某种模糊性,可以作多方面的理解外,含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这种含蓄具体反映到中国画方面,便是不能让人一目了然,而是必须“画尽意在”,有象外之趣。对此,浑南田有一段话说得极好。浑南田说:“春山如笑,夏山如怒,秋山如妆,冬山如睡。四山之意,山不能言,人能言之。秋令人悲,又能令人思。写秋者,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后埋藏能为之,不然,不若听寒蝉与魅蜂鸣也。”有“意”而又巧妙地“埋藏”之,使观者通过欣赏和体会产生共鸣,这便是艺术从创作到完成的全部过程。不过,以上关于诗意的分析,主要是画理方面的,而诗意要想成功地转换为画面的意境,则还需要通过外在的形态和笔墨,否则仍然只能是徒托空言。这种外在形态和笔墨,便是美学取向上的淡、清、静、远。这其中尤其是淡,乃传统中国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艺术趣味中的核心。翻开古人的画学典籍,诸如“平淡天真”、“天真幽淡”、“古淡天然”一类的用语触目皆是。因为尚淡,便自然地引出了清,清者,超尘拔俗之谓也,因此古人言山水,每每有“先观气象,后观清浊”之论。因为尚淡,又引出了静和远。“诗要孤,画要静”,这是中国传统艺术品评的一条重要法则,因为“孤”才能有品位,因为“静”才能有格调。而在古人的字眼里,远与玄是相通的,所以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对山水的观察以高远、深远和平远相标举。此外,不论是淡也罢,还是含蓄也罢,都又引出了暗和虚。董其昌说:“画画欲暗不欲明,明者如瓶棱钩角是也,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。”暗即不明,不明即有朦胧之美,因此董其昌又说:“摊烛作画,正如隔帘看月,隔水看花,意在远近之间。”暗和远皆有含蓄之意,而含蓄的画面则诗化的意境存焉,生动的气韵在焉,这是我们在欣赏中国画的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和认真体会的。
透过以上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诗意,或者说是诗化的意境与气韵生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虽然不能说一幅作品有诗意,便是气韵生动,但凡是气韵生动的作品,大多都有着葱花、浓郁的诗意,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。总之,形态笔墨、意境,这三者都与气韵生动关系密切,但它们中的任何孤立的一项都很难独自承担起气韵生动的重任,也许只有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,气韵生动,这一中国画品评标准中的最高要求,才有可能获得实现。
最后在结束本节之前,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声明,以上关于气韵生动的讨论,主要是针对传统中国画而言的,而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当代的中国画,则有很多作品未必相符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将在下文中继续讨论。
(文章来源:曹玉林《中国画欣赏》 未完待续)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